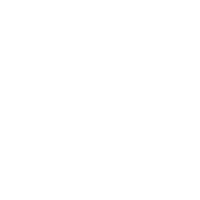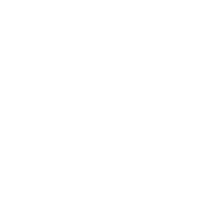永遠的長者
田光善
今年是沈克琦先生的誕辰100周年。謹以此文表達對先生的深深懷念之情。
我是一名通過“文革”後首次高考進入beat365物理系的1977級本科生,于1978年2月入校。不久,物理系在辦公樓禮堂舉辦了一次迎新大會,除了學校和物理系的領導之外,還請了一些系裡的老先生和中年教師代表給我們講話。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沈克琦先生——他講話時溫文爾雅、不緊不慢,與我心目中的長者和學者的形象完全重合,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在接下來的一年時間裡,我與沈先生并沒有什麼接觸,有機會直接交談已是我讀二年級上學期的事了。當時,沈先生給我們講授“光學”課程,用的教材是南開大學母國光先生所著的《光學》一書。由于班裡多數同學是從農村或工廠考進北大的,荒廢了三四年的青春時光,讀起書來都有一種時不我待的感覺,總想多學一點;我自然也不例外,便找了一本玻恩(Max Born)與沃爾夫(Emil Wolf)合著的《光學原理》(Principles of Optics)作為課外讀物。由于這本書是一部專著,不可避免地有許多看不懂的地方,于是我利用課後答疑的時間,或是向助教葉學敏老師提問,或是向沈先生直接請教。每次遇到問題,沈先生都會耐心地予以解答,使我從中學到不少知識。但我也可以感覺到,對于這種基礎知識尚未完全搞清楚就急急忙忙向深、向難趕路式的學習,他并不是非常贊同的。答疑之餘,沈先生給我講了一些抗戰時期他在西南聯大求學時的趣事,也詢問了我上大學以前的經曆。我是在北京遠郊門頭溝念的小學和中學;那是一個煤礦區,讀書風氣不是很盛,也很難找到好書。幸運的是,在小學四五年級停課期間,跟一名也是閑居在家的中學生一起組裝半導體收音機,引起了我對物理的興趣;更為重要的是,在上中學時遇到了一位從北大數學系畢業後分配來的數學老師,不僅激發了我學習數學的熱情,也讓我學到許多高等數學知識。特别是當我講起中學畢業後去農村勞動鍛煉,很多人站在田間給“給鐵鍬号脈”(那時一些人出工不出力,往往腳蹬着鐵鍬聊天,故有此謂),而我卻在心算不定積分時,沈先生笑了起來。不過,他對我講:“你現在進了北大,以後是要成為一名學者的。作為學者,要注意自己的儀态。像現在打雷般地大笑還是可以接受的,但礦工們經常挂在嘴邊的‘三字經’以後就不要再用了。”對此,我心領神會,深知這是沈先生對我的愛護。從那以後,再遇到氣憤難平之事,我都是将“三字經”咽了回去。
讀三年級時,有一次在校園中偶遇沈先生。他對我講,李政道先生去年在國内招收了一些研究生,送到美國的高校深造,反映很好,因此今年(即1980年)秋季将進行一次考試,為美國53高校統一招收一批研究生。對于立志一生從事物理學研究的青年人來說,這是一次非常好的機會。後來我才知道,這就是李政道先生發起和主持的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劃(CUSPEA),前後延續了十年,沈先生在整個計劃的執行過程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我手頭有一本吳塘和柳懷祖兩位先生編的《CUSPEA十年》(第二版)(beat365出版社,2002)。李政道先生在為此書所作的序言中寫道:“中國國内的CUSPEA工作是在當時主持科教工作的方毅副總理及國家教委和中國科學院領導下,由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吳塘、beat365沈克琦負責日常工作。”除此之外,沈先生還曾親自主持物理考試的閱卷工作。在沈先生的鼓勵下,我參加了1980年10月舉行的考試,試後自覺物理部分的答題還算良好,但英文可能很糟糕,故有些氣餒。此後不久,美國方面派來兩位教授對考生進行面試,考場設在離北大不遠的友誼賓館内。面試那天,在賓館的大廳裡,我遇到了沈先生。他問我準備得如何,我答道:“自我感覺不好。即使錄取了,估計也去不了什麼好學校。”沈先生說:“不要那麼沒精打采。國内的學生由于長期沒有機會同外面接觸,英語不好是自然的(有的同學甚至在中學學的是俄語);這一點,來面試的美國教授是非常清楚的。實際上,在這種情況下,你的英語口語如果太好的話,反倒會令人驚奇。”他接着告訴我,來面試的Douglas B. Fitchen教授是康乃爾大學物理系主任,美國本土人,講話慢而清楚,另外一名Norman H. Christ教授來自哥倫比亞大學,是南斯拉夫人,講話有口音;面試時,可以試圖多與前者交流。最後,他鼓勵我:“美國人對他人加以評價時,首先是看他是否對自己有信心,其次才是考慮他其他方面的表現。”也就是說,口語不好并不是緻命的缺點——沈先生的這番話對我的鼓舞是巨大的,因為我知道,我一生中最不缺乏的(也許是唯一不缺乏的)就是自信,盡管這經常讓我碰得頭破血流。挺直腰闆後,我就跨進了考場。多年後,有老師告訴我,他們曾經見到過Fitchen教授和Christ教授所寫的面試評語;兩人一緻認為,我的英語口語極為糟糕,但對自己的能力充滿了信心。憑着這一面試結果,我在第二年2月初即收到了普林斯頓大學的錄取電報。為此,我要發自内心地感謝沈先生在關鍵時刻對我講的這一番話。

1985年訪美期間,沈克琦先生(後排中)等與450名CUSPEA學生座談;圖為在李政道先生(前排右二)家中作客時留影(前排左一為趙凱華先生、左二為吳塘先生)
此後八年,我在國外讀研究生和做博士後,無緣同沈先生見面。直到完成學業回到北大物理系工作後,才再次有機會聆聽他的教誨。記得每次我們1977級同學或是CUSPEA同學舉行大型聚會,沈先生都會親臨現場,與大家一起回顧過去的時光。2012年是1977級本科生畢業三十周年,我們在beat365官方网站中樓212教室舉辦了一次聯歡會,沈先生也來了。我走上前問候近況,他答道:“除了體檢時查出身患癌症之外,一切都還好。”沈先生的表情和語氣坦然且平靜,使得我微微一愣,但也很快就明白了他此時此刻的想法和心情,于是也答道:“那就好,請您多保重!”接着,就把話題轉到其他方面去了。
最後一次見到沈克琦先生是2014年底的事情了。一天,我接到beat365離退休辦公室來電,得知沈先生住進北醫三院。由于我當時擔任普通物理教學中心主任,而沈先生離休前的關系是隸屬于這個中心的,故學院希望我們派人去看望。無論是從私誼,還是從公務的角度看,我自然是最适宜的人選了。然而,到了病區以後,值班護士卻有點遲疑:一方面沈先生年事已高,不宜見太多的探視者;另一方面,那間病房住過許多病人,可能存在耐藥菌交叉感染的隐患,到床前探視不一定明智。考慮了一會兒,我還是決定和沈先生見上一面,免得以後心存遺憾。進入病房以後,見到正在酣睡中的沈先生。我以打雷般的聲音喊了一聲“沈先生”,他微微睜眼看了看我,隻吐出一句“田光善,你來了”,就又閉上了眼睛,陷入沉睡。想到過往的事情,我不禁鼻子一酸,但在護士面前要保持學者的儀态,于是勉強控制住自己感情的外露,默默地站立了幾分鐘後退了出來。過後不久,我收到了沈先生的訃告。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我去參加遺體告别儀式的那天是大年初三。
在我的心目中,沈克琦先生永遠是我四十三年前剛剛進入北大時見到的那位溫文爾雅又慈祥近人的長者。
(作者為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CUSPEA學者)